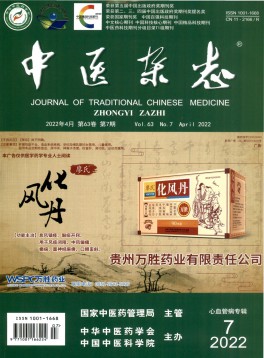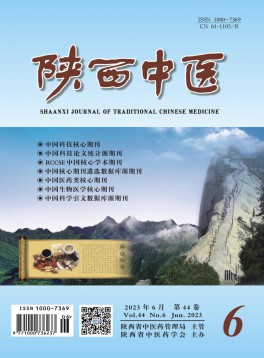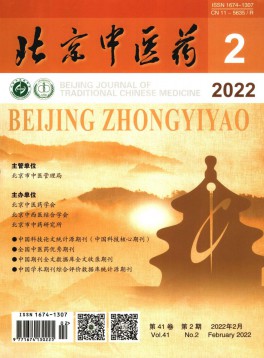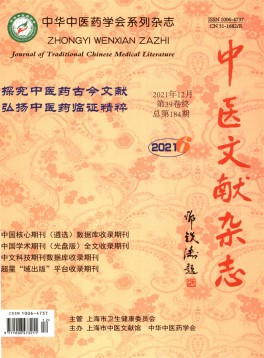中醫的哲學基礎模板(10篇)
時間:2023-07-24 16:14:42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醫的哲學基礎,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 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 所以, 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 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 因此, 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 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 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 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 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 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 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因此, 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 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 在這一研究進路中, 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 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 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 《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 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 也可以這樣認為, 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 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 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 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 ,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 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 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 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 論世間事跡, 褒君子, 貶小人, 以明治亂之所由, 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 醫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辭》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 ? 醫經與易經, 體同而用異, 拙集屢申其義矣。 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 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 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 假年學易, 不聞學醫, 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 不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 猶先于大道, 何故 ? 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 醫道也。 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 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 《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 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 因此, 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 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轉貼于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 ──“保性命者, 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 其表明, 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 對應和中者, 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 以藏象論之, 脾胃也 ,以五行論之, 中土也。以三焦論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體健康之象也 ,而離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 辨證者, 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達者; 中者, 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陰陽天地之間, 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 皆生五, 其氣三, 數犯此者, 則邪氣傷人, 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 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 時空對應之機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 ,精神乃治; 陰陽離決, 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 天地之道; 一開一和者, 動靜之機。”(吳謙: 《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 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 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 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 那么, 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 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 培養在中, 發用在上。”(鄭壽全: 《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于腎, 萌牙于肝, 培養于脾, 積貯于胸中為大氣, 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氣充足, 則署邪不能相犯 ;署氣入侵, 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 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腎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腎者也, 氣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 全身水道, 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 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 “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則萬化安, 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 “胃受司受納, 脾司運化, 一納一運, 化生精氣,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 以章虛谷為要, 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 為后天萬物之母, 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為太極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 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 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 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 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 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 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 因此, 醫易相通者, 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 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 因此, 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 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 宏觀而言, 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 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 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 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 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 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 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 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 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 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 但是, 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 筆者認為, 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 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 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 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 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 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 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篇2
中等專業學校是培養應用型“四有”人才的場所, 哲學基礎作為中專的一門德育基礎課,起著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三觀”、形成正確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至將來能更好地走向社會、為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中專生社會閱歷的局限,再加上長期以來人們在哲學教學上存在的一些誤區:比如對哲學功能認識片面化、教學模式拘泥于板塊化等等,使學生們普遍認為哲學語言晦澀難懂、哲學理論枯燥乏味、哲學內容嚴重與現實生活相脫節,從而扼殺了哲學自身的鮮活性,影響了學生學習哲學的積極性。所以在教學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是:這門課概念多而抽象,內容雜,學時少。怎樣上好這門課?我認為其實教師除了要具備較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較強的工作責任心外,教師采用的教學方法是否得當,直接影響教學效果。教學實踐表明:案例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方法,只要運用得當,對于提高教學質量、增強教學效果、以及對學生智力和能力的培養、人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案例教學及其特點
案例是實際存在或曾經發生過的、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例。案例教學是通過使學生經歷或體驗模擬的有一定典型意義的事物發生、發展的過程,來感悟和理解一定的道理和方法,獲得一定的知識的教學過程(教學方法)。哲學課的案例教學是通過使學生體驗或經歷對某一具體問題的認識、分析和研究的思維路線來感悟哲學的精神,理解哲學的原理,掌握哲學的方法,獲得哲學知識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案例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方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客觀真實。案例是客觀的真實的,客觀真實的東西就是最好的老師。學生對于理論的理解和掌握,是與認識論的原則一致的。客觀真實的案例和時事事件、現象等,是學生理論認知的感性基礎,容易被廣大學生所接受。
(二)典型直觀。案例教學法是一種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在具體實施中,往往是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即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分析研究來探尋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內在規律,從中導出一般的原理、理論,所以比較易懂好記,生動形象,有助于理論學習的進一步深化。例如講“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一框時,就可以設計以下案例:寓言《釘子》:“丟失了一個釘子,壞了一個蹄鐵;壞了一個蹄鐵,折了一匹戰馬;折了一匹戰馬,傷了一位騎士;傷了一位騎士,輸了一場戰斗;輸了一場戰斗,亡了一個國家。”通過非常形象的描述,揭示了哲學理論,加深了學生對普遍聯系觀點的認識。
(三)現實性和針對性強。為了使學生能夠主動參與學習活動,形成一定的學習能力、社會能力和職業能力。在教學中,要讓學生真正被擺到“學習主體”的位置上,在選擇案例的時候應貼近學生的現實生活。比如講本質和現象的關系時,就可以和學生講講網絡上的案件來切入到認識事物現象不代表認識事物的本質,通過學生自己的討論可以加深對真象和假象的理解,重新理解“眼見為實”的真正含義。
(四)吸引力和參與性強。由于案例和時事具有現實性和針對性,所以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情感,使之情動于衷而表于行。正因為如此才能激發學生的參與熱情,積極地展開討論、分析或辯論,充分展示他們的看法或觀點,促進他們對理論知識的掌握。比如在講“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時候可以從老子和孔子關于牙齒和舌頭的關系的對話入手,讓學生先有一定的好奇心,然后學生來用自己的想法進行分析,通過老師的點撥來完成哲學理論的理解,并且可以把這個故事放入人生觀教育中對學生進行人生哲理的領悟。
二、哲學課案例教學法的實施過程
哲學課的案例教學法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過程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在課堂上完成教學任務。哲學課的案例教學一般分三個步驟:
1、案例的準備和布置。案例是教學的主線,要貫穿一堂課的始終,能起到組織教學各環節的作用,比如導入、講解、討論、對話、總結等具體教學過程都以案例為基礎而展開,它是學生獲得認知的載體。所以,選好適用的案例對組織教學非常重要。案例的選擇要具有典型性、時效性、真實性。以“質量互變規律”這一問題為例;首先,教師根據教學進度和課程內容,安排學生閱讀有關的教學內容,并將相關案例材料交給學生做課前準備;然后學生按照老師的安排,認真閱讀相關內容,完成教師所布置的案例分析和論證。這部分內容將是教師以后在課堂上要濃黑重筆,充分展開論述的份量較重的內容。比如:“運用質量互變規律”的原理來分析我國申奧成功的問題,布置案例思考題是為了使理論學習落到實處,把重點放在應用上。
2、組織課堂教學。這是實施案例教學的關鍵和中心環節。首先是要呈現案例,可以在剛上課時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描繪案例內容,或給每個學生發放一份文字案例,也可借用現代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技術呈現案例,通過這些生動多樣的開場白,引起學生的關注,為以后展開的課堂教學打下了一個良好的鋪墊。其次,教師開始講解,分析他布置給學生的這一典型案例,隨著對整個案例進行過程的詳細分析,闡述這一案例中所揭示的事物產生,發展變化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哲學思想,緊扣書中主要內容,重點思想,從典型案例中提煉出與之相吻合的思想觀點來,這樣可以深化學生對抽象的理論的理解和把握。再次,在老師對案例分析,講解的基礎上,積極引導學生發言、討論,就自己所做的案例分析和老師講解的案例分析進行比較對照,或同學們之間相互比較分析,找出異同,區分正誤,達到啟發思維、充分開發學生智能的目的。在討論過程中,要讓學生充分發表意見,鼓勵不同觀點的爭辯,不單純地去追求一種正確答案,而是重視得出結論的思考過程。每個教學案例所涉及的問題都必須由同學們自己進行分析、解釋和討論,對學生思想上的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教師不應簡單否定,而應引導學生正確分析錯誤的實質以及產生錯誤的原因。在討論過程中,教師應有強烈的民主意識。以平等的身份參與組織和討論,啟發學生討論,切忌發號施令和批語指責。對于部分學生不愛發言或很少發言,教師要和顏悅色地啟發,開拓他們的思路,逐步消除他們的自卑感,使他們明確主人翁地位,從而產生積極參與討論的責任感。
3、評價案例。點評階段是案例教學的最后階段,往往是一堂課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教師必須通過學生的發言了解討論的效果,必須要求學生案例與理論結合起來,歸納出一般性的理論觀點,必須解決學生提出的疑難問題,并且在這基礎上教師能把一般的觀點進一步深化、拓展。可以表揚成績突出的同學,指出存在的問題有哪些,并精煉地概括出本案例所反映的主題思想和核心內容,提出從事案例分析的正確思路和一般方法,進而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的能力。應注意的是教師講評除了教育學生掌握一定的哲學原理、哲學知識外,關鍵是要教會學生運用這些哲學原理、哲學思想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學會分辯是非曲直、美丑善惡,懂得唯物辯證地思考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三、哲學課案例教學法的現實意義
哲學課采用案例教學法,可以避免傳統的教學中從理論到理論的空洞、抽象、乏味、說教式的教學弊端,將哲學理論與現實生活相結合,能夠使學生保持與現實世界或社會的廣泛接觸與緊密聯系,擴大自己的視野;有效地幫助學生建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學生的內在素質和能力。在具體的情境中滲透深奧的哲學理論,將哲學理論學習具體化、形象化、生動化,從而使學生產生一種新鮮感和強烈的求知欲,提高了學生學習哲學的積極性和自覺性,體現了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對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養成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案例教學法的實施和應用對教師的素質和理論水平也是一種錘煉和提高。但我們也必須看到案例教學法只是現代教學方法中的一種,要使哲學通俗化、趣味化,必須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廣泛運用各種教學手段,才能真正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哲學課堂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篇3
【摘要】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技術的發展,腦出血的發病率逐年上升。腦出血患者長期臥床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是壓瘡。中醫護理以整體觀作為指導思想,辨證施護。通過對壓瘡患者及壓瘡高危患者的生活起居、飲食調養、情志護理、功能鍛煉、中藥制劑等中醫護理技術的應用,達到有效防治壓瘡的目的。
關鍵詞 腦出血;長期臥床患者;壓瘡;中醫護理
【中圖分類號】R47【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9561(2015)07-0102-01
臨床資料 我院2009年1月—2010年12月因腦出血住院病人438例,均符合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疾病學術會議有關腦出血的診斷標準[1],經頭部CT或MRI檢查確診為腦梗死。其中腦出血后長期臥床患者繼發壓瘡范圍及部位不等病例28例。年齡56-92歲,其中偏癱25例,全身癱瘓3例。中醫認為,壓瘡的發生,在內是由于久臥傷氣,氣虛而血行不暢,久病而出現氣血虧虛;在外由于軀體重量對著褥點的壓迫及軀體著褥點的摩擦擠壓而致受壓部位氣血失于流暢,造成局部皮膚失養而壞死肉腐,形成瘡瘍[2]。隨著臨床護理經驗不斷積累,我院運用中醫護理技術在腦出血患者繼發壓瘡的防治工作中取得良好效果。
1一般護理
1.1 飲食護理: 中醫十分重視飲食的調養, 良好的膳食是改善患者營養狀況,促進瘡面愈合的重要條件。中醫飲食調護是根據中醫的“因人制宜”思想,審因用膳,辨證用膳,強調飲食的針對性。選擇適宜自身病情需要的飲食,可以增強臟腑功能,充盛氣血,對疾病有重要的輔助治療或治療作用。腦出血患者飲食調養原則是:飲食適量,定時定餐,不宜偏嗜。以清淡低鹽易消化為原則,忌肥甘辛辣食物,戒煙酒。意識障礙、吞咽困難者,可采用鼻飼。發生壓瘡的患者或壓瘡高危患者,多患有慢性疾病且需長時間臥床,飲食護理需兼顧原發疾病和壓瘡局部修復的營養需要,如心血管疾病患者,應給予高蛋白、低熱量、低膽固醇、低鹽飲食,多吃蔬菜水果,少食多餐。
1.2 生活起居護理:環境與休息:保持室內整潔安靜,空氣新鮮流通。春夏兩季陽氣活動旺盛,患者應著柔軟、寬大、吸汗的棉質衣物,注意保持皮膚的清潔干爽,及時清除汗液等分泌物;秋冬時節,陰氣轉盛,應注意幫助皮膚適當補充水分,增強皮膚抵抗力。勤整理床鋪,保持平整、清潔、干燥、無皺褶。鼓勵和協助臥床病人經常更換臥位,減少受壓時間,建立床頭翻身記錄卡。對有大、小便失禁,高熱汗出的患者,應隨時觀察皮膚情況,發現衣服、床單浸濕后要立即更換,并使 用氣墊床,避免壓瘡的發生,也有利于壓瘡的愈合。
1.3 情志護理: 腦出血后抑郁與情志密切相關,由于風瘀、痰、熱交搏郁結,,神明失其清展而情緒低落,出現抑郁[3]。對腦出血且繼發壓瘡患者或壓瘡高危患者來說,長期住院治療、對疾病的憂慮和疼痛的折磨,導致了患者的抑郁情緒。 中醫情志護理“情志相勝法”出自“內經”,是古代中醫學中最典型而系統的心理治療方法,是以五行相克為理論依據,用一種情志糾正另一種情志所致疾病的方法[4],即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喜勝悲,悲勝怒。護理人員給予疏導、解釋、安慰,調動患者的主觀能動性,減輕或消除不良情緒對疾病的影響, 有效改善了患者抑郁狀態,增強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
1.4 功能鍛煉:適當的運動有利于通暢氣血,活動筋骨,健腦強神,增強抵御病邪的能力。可根據患者的情況,采取早期良肢位擺放、定期翻身、指導患者適當進行床上運動、或為患者做恰當的被動運動,同時配合針灸、推拿等中醫療法,一方面有利于原發疾病的康復,另一方面幫助患者增強體質,盡早離開病床或輪椅,以降低壓瘡發生的機率,同時也有利于壓瘡的愈合。
2瘡面護理
2.1 對壓瘡進行全面評估,包括大小、原因、部位、程度及合并癥,制定護理計劃。病發部位初為淡紅色,腫、熱、有觸痛,此多為壓瘡的前驅期,用溫水擦浴受壓部位,擦背或用熱水進行局部按摩,定期用紅花油擦背或受壓部位,并配合適當的按摩,勤翻身促進局部血液循環,改善局部營養狀況,防止組織營養不良。
2.2 局部紅腫向外擴大、變硬,皮膚變為紫色,常在表皮有水泡形成, 保持局部清潔、干燥,用無菌注射器抽出水泡內液體,表面以聚維酮碘溶液消毒,涂以濕潤燒傷膏,并以神燈或鵝頸燈(60 W燈泡,距傷口25 cm)每日照射1~2次,每次10~15 min,或頻譜治療儀照射,每日1~2次,每次20~30 min。
2.3 局部皮膚色紫,漸趨潰破,浸及肌肉,腐爛壞死形成潰瘍。創面色鮮紅為正氣上充,內蘊熱毒,局部聚維酮碘溶液消毒,中藥金黃膏外敷每日2次。瘡面稍凹,邊緣微腫,中央生黃、綠色膿液,質稠氣臭,為熱毒蘊結,營血失調, 先以聚維酮碘溶液局部消毒,再清除壞死組織,生肌散外敷,每日1次。同時內服中藥以補氣養血。一般5~7天后創面組織向上及中央生長,新鮮肉芽組織生長良好,創面逐漸減少。
3小結
腦出血繼發壓瘡雖病在局部,但與整體密切相關。祖國醫學認為,壓瘡的病因病機是:局部受壓,氣血瘀滯,瘀血腐肉,破潰感染,熱毒至久,傷陰傷陽,經久不愈,氣血雙虧。患者一旦患上壓瘡,不僅痛苦不堪,而且其并發癥還會威脅到生命安全,尤其是重度壓瘡。因此,運用中醫護理的起居護理、飲食護理、情志護理、功能鍛煉、中藥制劑應用等方法,對腦出血患者繼發壓瘡的預防和治療不僅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而且將突顯中醫護理的優勢。
參考文獻
[1]中華神經學會,中華神經外科學會.各類腦血管論斷要點[J].中華神經外科雜志,1996:29(6):379.
篇4
A(美國外教): Hi, you have a pair of beautiful shoes.
B(中國學生): Thank you, my friend bought them for me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hem?
A: Oh, ye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B: Well, if you like them, I’ll ask my friend to buy another pair for you.
這里的美國朋友只是想禮貌性地稱贊一下對方的新鞋子,因為在西方文化中,對他人的新服飾或打扮表示欣賞是良好修養的一種表現。中國學生不了解這一點,熱情地要為對方買一雙一模一樣的鞋子,搞得對方哭笑不得。又如:
A(中國朋友): Hi, it’s so cold today, why do you only have a T-shirt? Aren’t you cold?
B(美國外教): I’m fine.
A: Put on a sweater. Otherwise you’ll get a cold.
B: Ok, Mom.
中國學生按照中國的習慣想表示自己對朋友的關心: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是這對于美國人來說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因為穿衣打扮純屬個人喜好,他人如此“關心”自己等于在說他不能自立,不能夠自己照顧自己。這對于崇尚個性獨立的美國人來說,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矛盾最后只能導致雙方的不歡而散。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學習英語必須同時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比如,過去中國人見面常常用“吃了嗎?”打招呼,那是因為在中國長期以來吃飯是人們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但是如果這樣與英美人打招呼,他們會以為這是在請他吃飯。因為英國人見面常說“天氣真好!是不是?”,這是因為英國的天氣變化無常,有時一天中甚至會出現猶如四季的變化,人們對天氣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覺,常常談論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了解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不會產生這些誤會。
綜上所述,文化知識對于英語教學和學習意義重大,教師在授課的同時應隨時滲透文化背景知識,這樣學生才能學得一門純正的外語。那么作為教師,怎樣才能有效地教授文化知識呢?
傳授文化知識的途徑
縱觀我國的英語教學,長期以來一直注重聽、說、讀、寫、譯幾項基本技能的訓練和培養。在具體教學中,對于英美文化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造成學生雖然掌握了基本的語言知識,卻不能真正流暢地運用這一語言,不能用英語深入、靈活、得體和有效地進行交際。針對這一狀況,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開設專門的有關文化知識的課程,使學生系統地學習所學語言國家的社會文化知識,如“英美概況”“跨文化交際學”“語言與文化”等課程。
2)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電腦、電影、電視等直觀教具了解英美文化。
3)充分利用外籍教師。從學習外語的角度來講,與講本族語的人接觸十分必要。通過與外教課上、課下的接觸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異。
4)在閱讀文學作品、報刊文章時,引導學生留心和積累文化背景、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知識。對于我國學生來說能夠出國留學親身體驗異國文化畢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閱讀就成為一條重要的了解文化背景的途徑。
篇5
2013年1月2日,我有幸通過廣西財政資助出國留學來到了美國西北角的華盛頓州的華盛頓州立大學。這是一所具有兩百多年歷史的高校,是美國久負盛名的研究型大學。因為華盛頓州立大學位于距離市區較遠的普爾曼小鎮,這里空氣清新,人口稀少,沒有過多的喧囂。但是,由于其歷史較為久遠,因此周圍分布有各類超市和餐廳,同時校園有對學生教工免費開放的公交車,學生生活相對國內高校更方便和舒適。
我在到達華盛頓大學的第二周開始連續多次旁聽了該校Charles Pezeshki教授的Design Clinic Internal Business課程,結合多年在國內高校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寫成了本文。本文不僅分析了兩國高校在教學軟硬件上存在的差異,更期望通過分析這種軟硬件差異折射出了兩國教育體系和教育理念的差別,希望對國內高校開展教學改革提供幫助。
1.中美本科課堂硬件差異
來到華盛頓州立大學機械與材料工程學院的EM154教室,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座椅擺放與國內高校不同。教室中所有桌椅可以移動,學生圍坐在桌子旁,自由組成小組,上課時學生可以面對老師,也可以背對老師,并沒有像國內高校中桌椅固定,學生一律面向老師而坐。
EM154教室面積大約在250平方米,當時上課學生人數為30人,每個學生桌面空間較大,學生大多帶筆記本電腦上課。教室開通無線網絡連接服務,隨時可以上網查閱各類資料。而國內高校大多數教室沒有無線網絡服務,學生很少帶筆記本電腦上課。
2.中美本科課堂軟件差異
在軟件建設方面,在我旁聽的這門課程中所有學生都加入一個叫Basecamp的網絡平臺,在這個平臺里面,所有學生都可消息,上傳資料,提出問題。老師也可以通過這個平臺消息,上傳資料,回答問題。這樣課堂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得到了拓展。也就是說,除了上課見面的時間外,其他時間同學們也可以自由交流,師生之間也可以自由交流。
另外,一個顯著的差別是在Charles Pezeshki的課堂上,他并不拘泥于講授知識,而是通過不斷提問的方式激發學生思考。他的問題往往較為簡單,目的在于讓學生思考,學生一旦回答出問題,他就立刻給予肯定,并且能及時叫出學生的名字。這樣學生感覺到自己得到了肯定,學習積極性立刻提高,學習情緒飽滿。
但是,在中國高校本科課堂中,老師還是凸顯出中心角色,老師認為自己是課堂的主宰者,而沒有把學生放在與自己平等的位置來看待。老師成了宣講者,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情緒較為低落。
3.中美教育理念差異
通過對比中美本科教育中軟硬件的差別,我們不難看出中美教育界在教育理念上的差異。過去有學者就一門課程的授課過程比較過中美教育理念的差異,但從軟硬件角度進行比較的文獻很少。[1—2]
首先,在美國教育界比較公認的是以學生為本的思想。學生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體,老師是為學生服務的。學生具有更多的權利提出要求。學生在課堂上自由地向老師提出問題。另外,他們并沒有限制本科學生的自由,允許本科學生出去調研,去工廠解決實際問題。然而,在國內,很多高校因為擔心學生的安全問題是嚴禁本科出去開展調研工作的。另外,國內教育界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思想,就是學生應該服從老師的指揮,學生無形中被認為是整個“學校等級制度”中的低層。這種觀念上的錯誤是很嚴重的,因為這會導致學生產生抵觸情緒。學生的很多訴求得不到滿足,這時學生會失去繼續學習的興趣和信心。
其次,教師對于學生的要求是希望他們能夠積極地思考,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希望學生能夠多提出問題,及時回答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問題會被認為是愚蠢的問題。他們認為“最愚蠢的問題就是沒有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都會積極思考,大膽提問。然而,在國內一些老師并不希望學生在課堂上提問題打斷教學進程,過多的問題會使老師無法按教學計劃開展教學。教師將完成教學計劃看做是其教學工作的核心,并沒有關注學生的需求和社會的需求。學生被培養成為不會提問題的人,他們只是默默接受老師傳授的知識,而沒有真正參與到主動學習中去。
再次,對于學生實踐教學環節的投入。在Charles Pezeshki教授的Design Clinic Internal Business課程中,學生被分成6組,每個組6人,要求完成企業提出的實際問題。企業給每一個組分配一個項目,提供1萬美元的資金支持。學生可以離開學校到企業與企業的負責人進行討論,討論如何能夠完成企業提出的任務。在這樣的實際鍛煉中,學生學會了獨立生活,學會了如何與人打交道,如何解決實際工程問題,如何在一個團隊中協作工作。然而,國內一些高校比較在乎教育成本,他們會認為投出資金讓學生外出調研會增加教育成本,另外,很多企業并不歡迎學生到企業實習,因為他們缺乏對學生的信任,在他們看來本科學生是沒有辦法完成一項現實的工程任務的。
通過分析和比較,不難看出:中美本科教育不僅在軟硬件方面存在差異,而且透過這種差異我們能看到兩國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別。這種差別來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差異。這不是說美國的所有教育理念都是好的,我們應該用一種批判的思想去學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所用。希望本文能給國內的教育工作者一些啟迪,為今后更好地開展教學工作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篇6
哲學領域關于天人關系的上述見解勢必會對傳統養生文化產生深刻影響,這一方面是由于養生學直接以人體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則在于傳統養生文化是以古代哲學作為自己的深厚底蘊。事實上,天人關系也確實在中國養生文化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視為傳統養生文化賴以生成的哲學基礎。
早在中國傳統養生理論的奠基作《黃帝內經》中就明確指出:“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經水》)又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可見古代養生家在天人關系學說的影響下,已經直觀地感覺到人類處在天地之間,生活于自然環境之中,只能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既然人類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也就與自然萬物之間存在一種相通相應的關系。所謂“人與天地相參”,強調的正是人與自然的統一關系。這種統一關系在傳統養生文化中,至少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得到充分印證。
1.人體的生理過程與自然界的運動變化存在同步關系。《靈樞》提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這就是說,人體的生理活動會隨著四季的交替而發生生長、收藏的相應變化。《素問?金匱真言》還認為:“東風生于春,病在肝”;“南風生于夏,病在心”;“西風生于秋,病在肺”;“北風生于冬,病在腎”。意思是說,人的內臟的生理功能分別與四季不同的風向相聯系,不同季節的風向往往會引起相應的內臟器管發生一定的病理反應。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人體的生理過程是與自然界的運動變化相同步的。
(2)人體與自然萬物同受陰陽五行法則的制約,并遵循同樣的運動變化規律,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人身法天象地,悉與天地造化同途。《素問》:‘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已閉。’又云:‘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廓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廓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故天地有晝夜晨昏,人身亦有晝夜晨昏:天地有晦朔弦望,人身亦有晦朔弦望。其間寒暑之推遷,陰陽之代謝,悉與天地胥似。’”上述觀點的核心,就是把天地視為一個大宇宙,把人體當一個小宇宙,大小宇宙之間存在著一種息息相關的對應關系。
(3)人與自然萬物有著共同的構成物質。我國古代哲學家大多認為“元氣”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基本物質。《老子》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就是指陰陽二氣沖蕩而化合成萬物。人類作為自然界的萬物之一,同樣也是由“元氣”化生而成的。《素問?寶命全形論》所說的“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正強調了人和萬物一樣,都是天地之氣合乎規律的產物。事實上,在傳統養生理論,特別是《黃帝內經》中,人的生命過程,包括生、長、壯、老、死等各個階段,都被歸結為“氣”的發生和聚散的必然結果。
也許正是因為古代養生家充分認識到了人與自然萬物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統一關系,所以無論在養生理論或實踐方面,他們都極力主張把研究人體與探討自然統一起來。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素問?舉痛》),正是上述主張的典型概括。
科學發展史曾經一再告訴人們,任何一門學科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哲學,都必然采用一定的認識方法,而所采用的哲學認識方法的性質又會對該學科的理論及實踐產生深刻影響。考察中國養生文化史可以發現,“天人合一”的觀念幾乎滲透到了其中的每一個角落。首先,“天人合一”是指“天道”與“人道”或自然與人事是相通、相類和統一的。也就是說“天人合一”論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天人相通,皆以“天道”,為“人道”之根本,天人是相互貫通的;二是天人相類,認為天人在形體性質上都是相似的。如《呂氏春秋?知分》曰:“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人既是天之陰陽所化生,故天人同類而相應。這便是古代養生家探討人體奧秘的理論武器。如前所述,“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在養生領域一般轉化成一種關于天地與人體各為一個相對獨立而又彼此對應的所謂“天人大小宇宙”理論。古代養生家往往依據這種理論,從觀察宏觀的外在大宇宙入手,來指導探索人體的內在微觀“小宇宙”。俞琰在《周易參同契發揮》中就指出“古之修丹者,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稽于人心;于是虛吾心,運吾神,回天關,轉地軸,上應河漢之昭回,下應海潮之升降,天地雖大,造化雖妙,而其曰月星辰之著明,五行八卦之環列,皆為吾攝入一身之中,或為吾之鼎器,或為吾之藥物,或為吾之火候。反身而觀,三才(日、月、星)皆備于我,蓋未嘗外吾身而求之他也”。至于《黃帝內經》對人體構造的認識,更是明顯地帶有“天人合一”哲學觀念影響的烙印。《靈樞?邪客》稱:“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總之,在《黃帝內經》作者看來,自然界這個大宇宙有什么,人體小宇宙也就必然會有一個部分或一種機能與其對應。這種對人體奧秘的認識,今天看來盡管包含了不少牽強附會的主觀臆測成份,但它的產生對于傳統養生理論和實踐方法的確立,無疑提供了一種直觀的理論依據。
篇7
腦出血是臨床常見的急危重癥,發病率和死亡率高,尤其是重癥病人30 d內死亡率高達30%~40%,預后極差[1]。本文通過對田黃沖劑組和常規治療組患者腦血腫、腦水腫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變化的觀察,來評價田黃沖劑的臨床療效,并探討田黃沖劑治療腦出血急性期的療效機理。
1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入選病例為2007-09~2009-05就診于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的自發性腦出血患者60例,男性38例,女性22例;年齡42~70歲,平均(51.6±7.2)歲;其中基底結區出血37例,腦葉出血18例,腦干出血5例;均為發病24 h以內者。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臨床表現、體征、出血量及合并癥等方面,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入選標準腦出血參照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通過的“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全部以CT確診[2]。且除外合并急慢性炎癥、腫瘤、凝血功能障礙、混合性卒中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療或手術者。
1.3分組治療方法60例患者隨機分為常規治療組(30例)和田黃沖劑組(30例)。兩組患者均采用脫水(選用天津百特醫療藥品有限公司生產的20%甘露醇,依顱高壓程度給予150~250 ml,每6~12 h靜脈滴注1次,連用3~7 d;若出血量
1.4指標測定
1.4.1腦血腫及水腫體積測定分別于發病當天、第3,7,14天對入組患者行頭顱CT掃描,計算腦血腫及腦水腫體積。腦血腫體積〔出血量(ml)〕=π/6×長(cm)×寬(cm)×高(cm);腦水腫體積(ml)=水腫帶體積-血腫體積(血腫及水腫帶體積的測定均按多田氏公式[3]計算)。
1.4.2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所有入選患者在入院當天和發病后第3,7 ,14,28天進行腦卒中量表(NIHSS)評分[4],評估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情況。
1.5統計學方法所有實驗數據均采用±s表示,采用SPSS 12.0統計軟件;兩個獨立樣本的比較用t檢驗。P
2結果
根據頭顱CT結果計算,無論是兩組間比較,還是同組不同時段比較,患者腦水腫體積與其血腫體積成正相關,均在第3天出現高峰。田黃沖劑組患者的腦血腫、腦水腫在第7天明顯減輕(常規治療組高峰延遲到第7天),而常規治療組患者腦血腫、 腦水腫在第14天才有明顯減輕;說明田黃沖劑組患者腦血腫和腦水腫的吸收優于常規治療組。見表1~2。
2.1ICH患者腦血腫體積情況在發病3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體積達到高峰, 在發病7,14 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逐漸減輕。在血腫達到高峰后,各時段田黃沖劑組腦血腫體積均較常規治療組減少。結果見表1。表1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腦血腫體積比較
2.2ICH患者腦水腫體積情況在發病3d時,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 在發病7,14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水腫均逐漸減輕。常規治療組患者腦水腫體積在第7天達到高峰后逐漸減輕。除發病3天其余各時段田黃沖劑組腦血腫體積均較常規治療組減少。結果見表2。表2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體積比較
2.3ICH患者NIHSS評分情況見從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分析,患者的NIHSS評分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在發病第3天達到高峰,隨著藥物治療病情轉歸而下降,呈逐漸遞減降低的趨勢。兩組患者神經功能缺損的改善在第7天開始,并于第14天田黃沖劑組顯示出了優勢;到第28天其療效田黃沖劑組仍然優于常規治療組。結果見表3。表3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NIHSS評分
3討論
腦出血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來自兩方面:一是不同部位的出血壓迫周圍腦組織,另一方面是血腫壓迫周圍腦組織后引起水腫,破壞腦組織引起功能缺失。對于腦出血的治療主要在于促進血腫吸收、抑制水腫形成及減少神經功能的缺損。急性期腦出血傳統的內科治療以脫水降顱壓、調節血壓、維持水電解質平衡等對癥治療為主[1]。腦水腫是急性腦血管病的共同病理過程,早期主要是細胞毒性水腫,后期則為血管源性水腫,水腫的形成又可加重循環障礙及缺血損傷,擴大缺血范圍,并最終導致腦疝形成,因此,阻止和消除腦水腫是治療急性腦血管病的關鍵[5~10]。中藥三七具有活血化瘀、化瘀而不傷正氣的藥效,三七用于治療血管性疾病,歷史悠久。《本草綱目》中記載,三七“主治止血、散血、定痛”,具有活血、祛淤、消腫、止痛等功效,且活血化瘀、化瘀而不傷正氣,臨床應用已有六百余年歷史,用于腦血管病的治療取得較好的療效,并且自三七中分離到的三七素,其止血作用優于止血環酸;其三七總皂苷不但具有保護腦細胞、減輕腦水腫的作用,還具有解痙鎮痛作用[11,12];大黃苦寒降泄,能泄火止血,制后收斂止血力更強,其主要有效成分大黃素、大黃酚和α-兒茶素能提高血小板的粘附性和聚集力,從而加速止血[13];以大黃為主治療出血性中風痰熱腑實證及其并發的上消化道出血、高熱已成為臨床常用方法之一,作為通腑法的必用藥,合理應用大黃對病情的愈后有重要意義。本課題將聯合應用田七大黃,以使加強田七保護腦細胞,減輕腦水腫及解痙鎮痛作用,配合大黃化痰通腑泄熱,釜底抽薪,解除風火上旋之勢,使邪有出路,從而達到解毒開竅、通腑泄熱、熄風化痰、活血通絡之效。
本研究發現,在發病初期, 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腦血腫體積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但兩組間血腫無明顯差異;在發病3 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且田黃沖劑組與入院時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出現繼發出血現象的患者較常規治療組多;在發病7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較前減輕,田黃沖劑組與第3天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對腦血腫吸收的治療效果好于常規治療組;在發病14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減輕,血腫均明顯小于發病第3天。在各時段進行組間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但我們發現在腦血腫達到高峰后應用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血腫體積均在各時間段低于常規治療的患者,同樣說明田黃沖劑具有減輕腦血腫的作用。
腦水腫的的趨勢同腦血腫基本相同,在發病初期, 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腦水腫體積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但兩組間水腫無明顯差異;在發病3 d時,田黃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且與入院時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出現繼發出水現象的患者較常規治療組多;在發病7d時, 常規治療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均較前減輕,田黃沖劑組與第3天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對腦水腫吸收的治療效果好于常規治療組;在發病14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水腫均減輕,水腫均明顯小于發病第3天。在各時段進行組間比較發病1,3 d均無統計學意義,在發病第7天及14天兩組間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說明田黃沖劑可能通過減輕腦水腫的起到治療作用。
對不同時間段的NIHSS評分進行比較,發現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NIHSS評分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在發病第3天達到高峰,隨著藥物治療病情轉歸而下降,呈逐漸遞減降低的趨勢。通過各組間比較我們發現,只有第28天的時候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田黃沖劑在對病人的功能康復的治療上具有遠期療效,雖然其它各時段治療組間及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但我們發現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臨床功能恢復要好于常規治療組且NIHSS評分也低于常規治療的患者,說明田黃沖劑同樣有助于改善腦出血患者的早期神經功能功能康復。在同組各時段的比較我們發現常規治療組與田黃沖劑組具有同樣的趨勢,即在發病第3天時神經功能損傷達到高峰,隨后逐漸好轉。田黃沖劑組在發病第14天時與高峰比較都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常規治療組在發病第14天時與高峰比較都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可以說明田黃沖劑在第14天時的治療效果,因此我們有待于進一步的觀察臨床療效,挖掘數據,擴大樣本量,采用更多更準確評價體系評價患者臨床功能及生活質量康復狀況以明確療效。
總之,本研究表明,田黃沖劑對急性腦出血早期預防血腫及水腫擴大,有明顯的療效,對比常規治療腦出血早期血腫及水腫擴大發生率明顯降低,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神經功能。結合前期研究表明田黃沖劑與常規西藥比較具有更好的改善癥狀作用[14] 。因此,田黃沖劑對急性腦出血早期抑制血腫擴大、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指導臨床治療該病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參考文獻
[1] 潘均喜.腦出血的治療進展 [J].海南醫藥,2009,20(5):290.
[2]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1995) [J].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29(6):381.
[3]Young FB,Weir CJ,Lees KR,et al.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with disability outcome measures in acute stroke trials[J].Stroke, 2005,36 :2187.
[4]Rosell A,Ortega-Aznar A,Alvarez-Sabin J,et a1.Increased brain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fter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human stroke[J].Stroke,2006,37:1399.
[5]王維治.神經病學[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149.
[6]唐偉,鄒颯楓.針刺預處理對腦缺血/再灌注大鼠腦水腫及腺苷水平的影響[J].中國中西醫結合急救雜志,2007,14(3):166.
[7]Su C. Y., Chen H. M., Kwan A. L., et al.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after hemorrhagic stroke in basal ganglia[J]. Arch Clin Neuropsychol, 2007,22:465.
[8]Nys G. M., van Zandvoort, M. J..Cognitive disorders in acute strok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determinants[J].Cerebrovasc Dis, 2007,23: 408.
[9]Fujita K, Kato T, Shibayama K.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17 beta-estradiol on neuronal apoptosis in hippocampus tissue following transient ischemia/recirculation in Mongolian gerbils via down-regulation of tissue transglutaminase activity[J]. . Neurochem. Res2006, 31:1059.
[10]Ko A C,Chen A Y,Hung V K,et a1.Endothelin-1 overexpression leads to further water accumulation and brain edema after middi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via aquaporin 4 expression in astreytic end-feet[J].J Cereb Blood Flow Metab,2005,25:998.
[11]高學敏.中藥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595,988,1104,1422.
篇8
The expression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and ADAM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QIAN Jin—xian*, LI Lei, LU Shi—qi, CHEN Gang,ZHAO Yi—ming. *Department of ICU,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North Campus), N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Suzhou 21500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U Shi—qi , Email: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s of dynamic changes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and 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ethods Twenty—nine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rom April 2010 through April 2011 were enrolled for retrospective study. The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3 sets of grouping: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DCI group) and non—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no DCI group),cerebral vasospasm group (CVS group) and no vasospasm group (no CVS group), and good prognosi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and another 2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CT, DSA, or/and CTA to identify the intracrani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resulted from aneurysm rupture. The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1) the time from onset to admission was longer than 72 hours or patient was in imminent danger of death; (2) patients had surgery, interventional o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utside the hospital; (3) patients were under the treatment of antiplatelet medicine such as aspirin, clopidogrel, or other anticoagulants such as warfarin, etc; (4) patients had blood diseases, impaired kidney or liver function, pregnant, or with recent infections. Venous blood were taken one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o determin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ADAMTS13 and vWF by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 was used to measure mean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VMCA).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 was measured before discharg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version 13.0 software.Results The levels of vW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CI group, CV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vWF between DCI group and no DCI group 1 day and 4 days after SAH ( P
【Key words】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eurysm subarachnoid hemorrhage;von Willebrand factor; ADAMTS13;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Cerebral vasospasm; Prognosis
蛛網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是常見的神經系統急危重癥之一,發病年齡相對年輕,其中顱內動脈瘤破裂是其發病的主要原因[1—2]。盡管最近幾十年,對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診斷方法、治療手段及圍手術期的管理取得長足的進步,但病死率仍高達45%,存活者也有著較高的致殘率,其中aSAH后4~10 d內發生的遲發性腦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DCI)是導致轉歸惡化的重要原因。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通過介導血小板與血管內皮下膠原黏附并進而形成血栓,在SAH中的作用日益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但是研究結論卻不盡一致[3—4]。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是一種在肝臟合成的金屬酶,通過降解vWF多聚體來減少血栓形成,而關于其在aSAH中的作用卻不甚明確。本文旨在通過動態觀察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變化,探討其在aSAH患者中的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0年4月至2011年4月入住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外科的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29例,其中男性12例,女性17例,年齡(53.03±11.19)歲。所有入選患者均經CT、DSA和(或)CTA檢查確診為顱內動脈瘤破裂致蛛網膜下腔出血,并在早期接受動脈瘤夾閉手術。登記臨床資料:姓名、性別、年齡、住院號、出血量、GCS評分、動脈瘤部位、意識障礙史、Hunt—Hess分級、改良Fisher分級等,臨床資料由兩位專科醫師獨立評判并進行綜合。排除標準:(1)入院時發病已超過72 h或即將死亡的患者;(2)在外院已接受手術、介入或內科保守治療的患者;(3)正在使用抗血小板藥物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其他抗凝藥物如華法林等;(4)有血液系統疾病、肝腎功能不全、近期有感染性疾病、孕期患者。對照組為正常健康體檢者20例,其中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齡(48.60±6.40)歲。將上述患者分為遲發性腦缺血組(DCI組)和無遲發性腦缺血組(無DCI組);腦血管痙攣組(CVS組)和無腦血管痙攣組(無CVS組);預后良好組和預后不良組。各患者組間治療無明顯差異。
遲發性腦缺血(DCI)診斷標準[5]:(1)新出現的局部神經功能障礙;(2)GCS評分下降2分以上;(3)腦梗死;排除顱內再出血或梗阻性腦積水引起。腦血管痙攣(CVS)診斷標準[6]:入院3 d至2周內行床旁超聲多普勒(TCD)檢查,如Vm MCA(大腦中動脈平均血流速度)>120 cm/s,同時計算Lindegaard指數,即同側MCA(大腦中動脈)與ICA(頸內動脈)顱外段Vm之比(LI)>3,則診斷為腦血管痙攣。預后分組標準[7]:入選患者在出院時進行GOS預后評分(1分:死亡;2分:植物生存;3分:重度殘疾;4分:輕度殘疾;5分:恢復良好)。其中將GOS評分為4~5分病例記為預后良好組,GOS評分為1~3分記為預后不良組。
1.2 方法
對所有患者分別在SAH后1、4、10 d各采肘靜脈血5 ml,分別加入枸櫞酸抗凝管中,3000 r/min離心10 min后提取血漿,—80 ℃冰箱貯存備用。健康對照組每例取外周靜脈血5 ml, 方法同上。血漿vWF抗原含量與ADAMTS13活性(試劑盒購自蘇州大學血液研究所)測定均采用雙抗體夾心固相酶免疫試驗(ELISA)。SZ—125抗體、SZ—129抗體由蘇州大學血液研究所提供。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 )表示,并行成組 t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以 P
2 結果
2.1 臨床結果
在入選的29例患者中,動脈瘤部位:大腦前動脈瘤4例,大腦中動脈瘤2例,前交通動脈瘤10例,眼動脈瘤2例,頸內—后交通動脈瘤6例,大腦后動脈瘤1例,頸內動脈瘤4例。Hunt—Hess分級:Ⅰ級5例, Ⅱ級9例,Ⅲ級10例, Ⅳ級 4例,Ⅴ級0例。改良Fisher分級:0級0例,1級6例,2級12例,3級8例,4級3例。意識障礙史:短暫意識障礙6例,意識障礙持續大于30 min 7例,持續昏迷 4例。其中發生DCI患者6例(20.69%),發生CVS患者20例(68.97%),預后不良者共計10例(34.48%),有4例患者死亡,其余6例患者均伴有重度殘疾或呈昏迷狀態。發生DCI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66.67%),發生CVS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20%)。
2.2 血漿vWF水平的動態變化
健康對照組血漿vWF水平為(1.26±0.46)U/ml。DCI、CVS及預后不良組患者中1、4、10 d 血漿vWF水平均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P
2.3 血漿ADAMTS13活性的動態變化
健康對照組血漿ADAMTS13活性為(56.32±15.47)%。在發生DCI患者的1 d血漿ADAMTS13顯著低于健康對照組(P
3 討論
aSAH好發于Willis動脈環周邊較大的動脈分叉處,因其有再出血及出血后導致的腦損害如CVS、DCI、腦水腫和梗阻性腦積水等病理改變,所以有著較高的病死率和致殘率。其中aSAH后4~10 d內發生的DCI是導致轉歸惡化的重要原因[8]。但是對于DCI的確切發病機制仍不甚明確,最初一度認為aSAH后近端腦血管痙攣和管腔狹窄是DCI發生的“唯一”原因,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aSAH后CVS高達70%,其中只有30%發生DCI,并且在這部分患者中臨床癥狀與發生血管痙攣的血管分布并不一致[9—10]。此外,并不是所有發生DCI的患者都有血管造影腦血管痙攣的證據。隨后“廣泛微血管痙攣”[11]、“皮層擴散性抑制”[12—13]、“內皮細胞激活”[14—15]、“炎癥反應”[16—17]、“凝血級聯反應和纖溶失衡”[18]、“微血栓形成”[19]等學說相繼提出,在aSAH后DCI的發病過程中均扮演著不同程度的角色。但是目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微血栓形成”是DCI重要的發病機制之一,也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并且在尸解中也得到了證實[20]。
vWF主要來源于血管內皮細胞的W—P(Weibel—Palade)小體和血小板的α顆粒,介導血小板與血管內皮下膠原黏附并進而形成血栓,其分子量越大,與膠原和血小板的結合能力就越強[21—22]。ADAMTS13是一種金屬蛋白酶,主要在肝臟合成,主要作用于vWF第842位酪氨酸與843位蛋氨酸之間的肽鍵,從而降解vWF多聚體來減少血栓形成。Frijins等[23]研究提示,SAH后早期(72 h內)vWF濃度升高與DCI的發生相關,并且是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并不是CVS的獨立危險因素,可能由于vWF是小血栓形成的誘因,從而導致缺血性改變。ADAMTS13活性下降最初是在血栓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 (TTP)的研究中發現,近年來在心腦血管疾病中的作用也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但是關于ADAMTS13在腦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較少,最新的研究發現,vWF抗原升高與ADAMTS13 活性下降導致患者發生腦梗死的風險增高, ADAMTS13降低患者較ADAMTS13較高患者發生腦梗死的風險增加接近2倍[24]。國內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與之相似,在急性心肌梗死和腦梗死患者中ADAMTS13 活性較健康對照組顯著下降[25]。2009年Vergouwen等[26]研究也首次發現在aSAH后并發DCI患者中ADAMTS13活性下降,但是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下降之間并無相關性( r =—0.027, P =0.736)。但是由于DCI的發生更多是由于腦血管局部微循環障礙引起,所以vWF、ADAMTS13變化規律并不同于大血管病變所致腦梗死。
在本實驗中入選的29例患者中,發生DCI患者有6例(20.69%),其中發生DCI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66.67%),有2例未發生CVS(33.33%),而發生CVS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20%),發生DCI合并CVS 4例患者均預后不良。這些臨床數據表明,aSAH患者DCI的發生與否與預后密切相關, CVS與DCI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但是在DCI患者中并不是所有患者均發生了CVS,在CVS患者中也并未均進展成DCI。
本研究中DCI患者vWF抗原水平在1、4 d時均明顯高于未發生DCI組。ADAMTS13活性在第1天出現明顯下降,明顯低于正常水平及未發生DCI組。提示在aSAH患者早期可能由于ADAMTS13活性下降,導致ADAMTS13不能有效降解vWF成小分子片段,vWF多聚體在血管內聚集,形成微血栓,從而表現出血漿vWF抗原升高。而內皮細胞激活同樣可以引起vWF抗原的升高,但是本研究中發現DCI患者早期同時伴隨著ADAMTS13活性下降,所以我們認為在發生DCI患者中微血栓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CVS患者血漿vWF水平持續升高,在4 d時明顯高于未發生CVS患者,可能是與該時間點正好是CVS開始啟動的危險期有關,而在1 d時及后期未表現出差異,表明vWF水平在CVS發生的危險期中明顯升高,這是由于內皮損傷致CVS發生所致。早期血漿vWF水平與ADAMTS13活性下降不僅與DCI發生有關并且與預后相關。研究發現,通過檢測SAH患者血漿和腦脊液中vWF 濃度發現,SAH并發腦血管痙攣或腦梗死患者中血漿和腦脊液中vWF均明顯升高,腦脊液中vWF 水平與神經功能狀況呈正相關,因此vWF 可以作為預測CVS和局灶性缺血的獨立危險因素[21]。Frijns 等[14] 在測定106例aSAH患者早期(3 d內)血管內皮細胞激活標志物時,發現內皮細胞激活的特異標志物vWF與DCI的發生及預后相關,由于vWF升高導致腦循環中微血栓形成,引起缺血事件發生。
總之,通過本研究發現微血栓形成是aSAH后并發DCI重要發病機制之一,動態監測早期血漿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可以預測DCI發生,并且對aSAH預后的判定起著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本研究由于樣本量較小,缺乏中長期的隨訪治療,故仍有待大樣本多中心的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Ingall T, Asplund K, Mahonen M, et al. A multinational comparison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epidemiology in the WHO MONICA stroke study[J]. Stroke, 2000, 31(5): 1054—1061.
[2]錢進先,李磊,虞正權,等. 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早期預后多因素分析[J]. 中國急救醫學,2010, 30(1):297—300.
[3]Beuth W, Kasprzak H, Wozniak B, et al. Von Willebrand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Neurol Neurochir Pol, 2001, 35 Suppl 5: 130—134.
[4]Frijns CJ, Kasius KM, Algra A, et al.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aemia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 77(7): 863—867.
[5]Hop JW, Rinkel GJ, Algra A, et al. Initial loss of consciousness and risk of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troke, 1999, 30(11): 2268—2271.
[6]Jarus—Dziedzic K, Bogucki J, Zub W. The influence of ruptured cerebral aneurysm localization on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evaluated by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J]. Neurol Res, 2001, 23(1):23—28.
[7]Sandalcioglu IE, Schoch B, Regel JP, et al. Does intraoperative aneurysm rupture influence outcome? Analysis of 169 patients[J]. Clin Neurol Neurosurg, 2004, 106(2): 88—92.
[8]Roos YB, de Haan RJ, Beenen LF, et al. Complications and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 a prospective hospital based cohort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0, 68(3): 337—341.
[9]Weidauer S, Lanfermann H, Raabe A, et al. Impairment of cerebral perfusion and infarct patterns attributable to vasospasm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 prospective MRI and DSA study[J]. Stroke, 2007, 38(6): 1831—1836.
[10]施小燕. 重視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后遲發性腦缺血[J]. 中華急診醫學雜志,2010,19(12):1237—1239.
[11]Ohkuma H, Itoh K, Shibata S, et al.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intraparenchymal arterioles after experiment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dogs[J]. Neurosurgery, 1997, 41(1): 230—235.
[12]Leng LZ, Fink ME, Iadecola C. Spreading depolarization: a possible new culprit in the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Arch Neurol, 2011, 68(1): 31—36.
[13]Dreier JP, Ebert N, Priller J, et al. Products of hemolysis in the subarachnoid space inducing spreading ischemia in the cortex and focal necrosis in rats: a model for delayed ischemic neurological deficits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J]. J Neurosurg, 2000, 93(4): 658—666.
[14]Frijns CJ, Fijnheer R, Algra A, et al. Early circulating levels of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 associations with cerebral ischaemic events and outcom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 77(1): 77—83.
[15]Kessler IM, Pacheco YG, Lozzi SP, et al. Endothelin—1 levels in plasma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vasospasm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urg Neurol, 2005, 64 Suppl 1: S1: 2—5.
[16]Kasius KM, Frijns CJ, Algra A, et al. Association of platelet and leukocyte counts with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Cerebrovasc Dis, 2010, 29(6): 576—583.
[17]Hendryk S, Jarzab B, Josko J. Increase of the IL—1 beta and IL—6 levels in CSF in patients with vasospasm following aneurysmal SAH[J]. Neuro Endocrinol Lett, 2004, 25(1/2): 141—147.
[18]Roos YB, Levi M, Carroll TA, et al. Nimodipine increases fibrinolytic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troke, 2001, 32(8): 1860—1862.
[19]Vergouwen MD, Vermeulen M, Coert BA, et al. Microthrombosis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 additional explanation for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J].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8,28(11):1761—1770.
[20]Stein SC, Browne KD, Chen XH, et al. Thromboembolism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 autopsy study[J]. Neurosurgery, 2006,59(4):781—787.
[21]Chauhan AK, Kisucka J, Brill A, et al. ADAMTS13: a new link between thrombosis and inflammation[J]. J Exp Med, 2008,205(9):2065—2074.
[22] 錢進先,陸駿灝,陸士奇,等. 嚴重肺挫傷患者馮·維勒布蘭德因子、IL—8的動態變化及其意義[J]. 中華急診醫學雜志,2011,20(6):20—24.
[23]Frijns CJ, Kasius KM, Algra A, et al.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aemia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77(7):863—867.
[24]Bongers TN, de Maat MP, van Goor ML, et al. High von Willebrand factor levels increase the risk of first ischemic stroke: influence of ADAMTS13, inflammation, and genetic variability[J]. Stroke, 2006, 37(11):2672—2677.
[25] 董寧征,劉芳,季順東,等. 急性心肌梗死和腦梗死患者血漿中ADAMTS13的測定及意義[J]. 中華血液學雜志,2008, 29(3):161—163.
[26]Vergouwen MD, Bakhtiari K, van Geloven N, et al. Reduced ADAMTS13 activity in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9,29(10):1734—1741.
(收稿日期:2012—06—11)
DOI: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2.09.019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1100872)
作者單位: 215000 江蘇省蘇州,南京醫科大學附屬蘇州市立醫院北區ICU(錢進先);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外科(李磊、陳罡),急診科(陸士奇),血液研究所(趙益明)
篇9
中圖分類號:R651.1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533(2015)01-0033-04
Expression of D-D, hs-CRP protein in the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progressive hemorrhagic injury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ZHU Fang1*, ZHANG Li1, CHEN Han1, LIU Shaohua2
(1.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Jiangxi Pingxiang Mining Group, Jiangxi 337000, China; 2. Clinical Laboratory,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of Pingxiang City, Jiangxi 337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D-dimer (D-D) and high 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in the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progressive hemorrhagic injury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Eighty-seven patients diagnos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09 to December, 2013 were selected as an injury group, which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mild, moderate or severe subgroups based on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 and excellent, good or poor subgroups based on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 Meanwhile, 10 healthy persons were selected as a control group. D-D, hs-CRP levels in all subjects were measured by immune turbidimetry and both GCS and GOS scores were performed in the injure group. The relationship of D-D , hs-CRP levels and GCS, GOS with etiolog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D-D and hs-CRP levels were obviously higher in the injury group, severe subgroup and poor subgroup than in the healthy group, mild and moderate subgroups and good and excellent subgroups in turns, respectively (P<0.05).The analysis of Spearman showed that D-D and hs-CRP levels were all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CS, GOS. Conclusion: D-D and hs-CRP level in plasma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intracranial progressive hemorrhagic injury and early detection can help doctors understand th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KEY WORDS D-dimer;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on protein; hemorrhagic lesions
顱腦外傷常見致病原因有運動性撞擊、高空墜落、機動車碰撞等,主要臨床表現為意識障礙、頭痛、瞳孔散大和血腫等癥狀,且易發生或并發各種出血性疾病,加重患者的傷情[1]。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是指顱內各種出血性疾病經影像學或手術檢查證實原發出血部位發生更嚴重的出血癥狀或并發新的出血部位,屬于顱腦外傷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2]。此外,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可致使顱腦外傷患者缺血缺氧的發生,并進一步損害腦組織和神經組織,致使患者病情加劇惡化,增加患者傷殘率和死亡率[3]。因此,早期診斷顱腦損傷患者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可助于醫師了解和掌握患者病情,及時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治療方案,以降低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給患者帶來的各種不良風險[4]。我院通過檢測患者血漿中D-二聚體(D-dimer, D-D)和超敏 C-反應蛋白(high-sensitive creative protein, hs-CRP)表達水平,探討其與顱腦損傷合并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病情和遠期治療等聯系,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10月-2013年12月期間我院確診治療的顱腦損傷合并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患者87例作為顱內損傷組,其中男46例,女41例,年齡24~67歲,平均年齡(37.94±12.65)歲,高空墜落22例,運動性撞擊23例,機動車碰撞42例,依據GCS評分分為輕度亞組(12~14分)24例、中度亞組(9~12分)45例和重度亞組(3~8分)18例,依據GOS評分分為優秀亞組(5分)24例,良好亞組(4分)45例,不良亞組(2~3分)18例,無死亡病例,同期選取體檢健康人員10例作為健康組,其中男5例,女5例,年齡26~63歲,平均年齡(35.38±23.81)歲,所有受試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且經我院醫藥倫理會審批通過,2組受試者在年齡、性別等基本資料對比無顯著差異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一般資料具有可比性。
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5]:①經顱腦CT檢測證實符合顱腦損傷和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標準;②無其他部位嚴重性損傷;③無血液系統損傷;④傷前3個月內無感染性疾病史。排除標準:①伴有心、肝、腎等重要臟器嚴重性疾病;②有精神疾病史;③有其他慢性疾病史;④單獨患有顱腦損傷或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疾病患者。
方法
對所有受試者給予早晨空腹措施,于手臂抽取靜脈血4 ml分別平均置入2試管中:一管2 ml置于凝血常規抗凝管中混勻,離心取血漿測D-D; 另一管2 ml置于血常規抗凝管中混勻,取全血測hs-CRP[6]。D-D水平測定采用SYSMEX CS-2000i全自動凝血儀及原裝配套D-D試劑,hs-CRP水平測定采用由韓國BodiTech Med Inc公司生產的hs-CRP濃度測定試劑,所有操作均嚴格遵從說明書和相關規定進行。參照說明書標準對D-D、hs-CRP水平進行判定并統計分析,對顱內損傷組患者治療前后應用格拉斯哥昏迷評分(Glasgow Coma Scale,GCS)和格拉斯哥預后評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進行病情、遠期治療等情況評定,分析D-D、hs-CRP水平與顱腦損傷合并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的關系。
觀察標準
GCS評分[7]15分為正常、9~14分為輕度昏迷、3~8為中度昏迷、低于3分為嚴重昏迷; GOS評分[8]低于2分為死亡、2分為植物性生存、3分為無法生活自理、4分為需他人協助但可獨立生活、5分為有自理障礙但無需他人幫助、5分以上為正常。
統計學數據處理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多組資料之間采用F檢驗,對D-D、hs-CRP水平與顱腦損傷合并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的關系應用Spearman分析法分析,P<0.05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顱內損傷組和健康組患者血漿中D-D、hs-CRP水平對比
顱內損傷組患者血漿中D-D、hs-CRP水平明顯高于健康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輕度、中度和重度亞組間D-D、hs-CRP水平對比
重度亞組患者血漿中D-D、hs-CRP水平最高,中度亞組次之,輕度亞組最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優秀、良好和不良亞組D-D、hs-CRP水平對比
不良亞組患者血漿中D-D、hs-CRP水平最高,良好亞組次之,優秀亞組最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
顱內損傷組患者血漿中D-D、hs-CRP水平與GCS、GOS和發病原因的Spearman分析
Spearman分析結果顯示,D-D和hs-CRP水平均與GCS、GOS呈負相關(表4)。
討論
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是致使顱腦損傷患者殘障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導致患者傷情加重,與患者的預后具有較為密切的聯系[9]。因此,早期準確診斷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可有助于醫師對患者進行風險評估,利于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以降低各種不良情況的發生[10]。D-D屬于纖維蛋白單體在活化因子交聯后由纖溶酶水解反應下的一種特異性降解產物,對纖維蛋白溶解功能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可靠性[11]。hs-CRP屬于血漿中具有高靈敏性的一種C反應蛋白,可有效準確反應低水平炎癥狀態,可作為心血管事件危險最重要的預測因子之一[12]。有研究表明 [13],通過檢測顱腦損傷患者血漿中相關因子水平可預測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的發生,對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通過檢測和分析顱腦外傷合并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患者和健康人員血漿中D-D、hs-CRP水平,發現顱腦外傷合并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患者血漿中D-D、hs-CRP水平呈現高表達,且患者病情越嚴重,血漿中D-D、hs-CRP水平越高。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使顱腦外傷患者的應激反應更為劇烈,致使顱內血小板積聚增多,導致血管中血液流通不暢,同時持續和二次出血性損傷使腦組織不斷釋放各種凝血活性因子,使患者凝血功能出現紊亂導致血流凝血和纖溶系統平衡失調;此外,凝血系統紊亂使患者處于高凝狀態,血管破裂引起的炎癥反應可使CRP補體復合物沉積于動脈壁內,CRP與脂蛋白相互作用下會激活補體系統,產生并釋放大量自由基對腦部組織造成損傷,加重了患者的病情。因此,血漿中D-D、hs-CRP水平升高對顱腦外傷合并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具有重要的診斷價值,有效反映了患者的病情。此外,GCS、GOS評分作為患者病情和預后的重要臨床標準之一,通過Spearman分析結果發現,血漿中D-D、hs-CRP水平與患者的病情和預后具有密切的聯系,患者血漿中D-D、hs-CRP水平越高,顱內損傷和出血性損傷程度越高,預后水平越低,醫師應當及早積極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法和方案,以提高患者的治療效果和預后水平。
綜上所述,早期檢測血漿中D-D、hs-CRP水平對顱腦外傷合并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具有重要的診斷價值,可有效反映患者病情和預后水平,提示醫師應當積極對患者及時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治療方案,以提高疾病的治療和預后療效。
參考文獻
焦薇, 周脈濤, 吳文華, 等. 右美托咪定與咪唑安定對重型顱腦外傷患者圍術期炎癥反應及顱內壓的影響[J]. 中國現代醫學雜志, 2014, 24(17): 34-38.
沈合春, 錢志遠, 鄭達理, 等. 急性顱腦損傷后進展性出血性損傷極高危因素分析及定時復查CT時間探討[J]. 中華神經醫學雜志, 2011, 10(7): 735-740.
辛志成, 龍連圣, 張建忠, 等. 腦外傷后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的影響因素分析[J]. 中國綜合臨床, 2009, 25(11): 1183-1184.
馬輝, 錢志遠. 外傷后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的相關因素分析[J]. 山東醫藥, 2009, 49(2): 60-61.
黃文飛, 黃啟銳, 郭祚國. 顱腦外傷后進展性出血損傷的臨床分析[J]. 廣州醫學院學報, 2009, 37(6): 59-61.
秦國強, 彭才祖, 王冠, 等. 重型顱腦外傷并膿毒血癥患者的血清TF、TFPI、hs-CRP變化及意義[J]. 山東醫藥, 2014, 54(5): 39-40.
馬濤. 開顱手術治療80例重癥顱腦外傷的臨床療效觀察[J]. 現代診斷與治療, 2013, 24(20): 4651-4652.
于鳳穎, 王穎. 顱腦外傷患者凝血功能與GCS、GOS評分的關系[J]. 中國醫藥導刊, 2012, 14(6): 969-970.
張施遠, 石海平, 曾春, 等. 82例顱腦創傷后進展性出血性損傷療效分析[J]. 創傷外科雜志, 2014, 16(3): 257-257.
袁劍雄, 黃新. 顱內進展性出血性損傷早期診斷的研究進展[J]. 大眾科技, 2013, 15(5): 144-146.
何恩萍, 吳家梅. 急性顱腦損傷患者血漿D-二聚體測定的臨床意義[J]. 內蒙古中醫藥, 2013, 32(28): F0002.
王連運, 王光民. 重型顱腦損傷患者血清高敏C-反應蛋白、D-二聚體的變化及其意義[J]. 中國臨床神經外科雜志, 2014, 19(4): 209-211.
篇10
[中圖分類號] R743.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210(2010)11(a)-012-04
Study on the content changes o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REN Bin1, CHEN Laizhao2, GUO Tao1
(1.Clinical Department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in acute stage,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Samples of serum and CSF were examined on day 1,3,7 and 14 after onset in 40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Clinical outcome was assessed on the 30th day after onset with the Glasgow Outcome Scale(GOS)and Glasgow Coma Score (GCS). Results: The levels of NSE in hemorrhagic stroke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It reached maximum within 3-7 days, and decreased within 7-14 days.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onset (within 14 days), the more severe the condition at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s, the lower GCS score, the value of NSE was higher (P<0.001); the levels of N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in the excellent prognosis group increased,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erences between the excellent prognosis group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 (P<0.05); in the same patient, the value of NSE in CSF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e serum one (P<0.05). The contents of NSE in serum and CSF in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r=0.966,P<0.05). Conclusion: It indicates that NSE may serve as quantitative biochemical markers, and its levels may reflect the degree of brain damage. As well as, it may prove to be an index of monitor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Key words] Hemorrhagic stroke; Serum; Cerebrospinal fluid(CS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
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相對分子量為78 kD,是烯醇化酶的一種同工酶,特異性地存在于大腦神經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中,是神經元的標志酶。在一些腦損傷性疾病中,如腦卒中、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外傷、癲癇等,都曾發現患者的血清和(或)腦脊液NSE濃度升高[1-5]。NSE作為判斷中樞神經元損傷程度的重要參數,近年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臨床和科研工作者的關注。本文通過對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的血清和腦脊液NSE水平進行動態檢測,觀察二者NSE水平的動態變化及其關系,探討NSE在出血性腦卒患者病情發生、發展及預后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5月~2010年10月我院神經外科收治的40例出血性腦卒中患者,其中,男20例,女20例;年齡40~84歲,平均(59.8±9.6)歲。全部病例均為首次發病,而且在起病24 h內入院,診斷全部符合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修訂的診斷標準[6],并均經頭顱CT或MRI檢查確診。排除合并有腦外傷、惡性腫瘤、繼發性腦出血(腫瘤出血、顱內動脈瘤、動靜脈畸形等)、嚴重心功能不全及慢性腎衰、以及既往有腦中風或癲癇病史者。各組之間性別和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2 實驗方法
1.2.1取材 40例患者均于入院24 h內及第3、7、14 d的凌晨空腹采集外周靜脈血和腦脊液各2 ml,每一相對應的血液和腦脊液標本的采集時間相差不超過1 d。采集標本后迅速常溫離心(3 000 r/min)10 min,分離后取上清液置于-80℃備檢,避免反復凍融。如有溶血標本則棄之。
1.2.2分組 所有患者入院后按格拉斯哥昏迷計分法(GCS評分標準)分為兩組:GCS 3~8分組和GCS 9~15分組。
以格拉斯哥預后量表評分(GOS評分)評定患者發病30 d時的預后:死亡,1分;植物人生存,長期昏迷,2分;重度病殘,需他人照顧,3分;中度病殘,生活能自理,4分;恢復良好,能正常生活,5分。GOS 1~3分為預后不良組,GOS 4~5分為預后良好組。
1.2.3 NSE檢測方法 應用ELISA法檢測血清和腦脊液NSE濃度。NSE-ELISA試劑盒由上海領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采用長春賽諾邁德醫學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的自動酶標分析儀SPR-960進行檢測,嚴格按照試劑盒使用說明書進行操作,最后結果根據標準曲線換算成實際濃度。標本均為復孔檢測。NSE單位為ng/ml。
1.3 統計學方法
本實驗在SPSS 13.0統計軟件下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量資料的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或秩和檢驗,兩兩比較用LSD或Dunnett T3。變量間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或Spearman秩相關檢驗,以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血清及腦脊液NSE變化規律
NSE水平在發病后的不同時間(24 h內,第3、7、14 d)之間比較,第3天和第7天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余各時間點相互間比較差異均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01)。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14 d內)四個時間點血清和腦脊液NSE的平均水平均于起病后3~7 d達高峰,7~14 d逐漸下降(表1、2)。
表1 各評分組不同時間點血清NSE的比較(x±s,ng/ml)
Tab.1 Comparison of serum NSE in different time points between the two GCS scores (x±s,ng/mlm)
與24 h比較,*P<0.001;與3 d比較,P<0.001;與7 d比較,P<0.001。與GCS 9~15分組同一時間比較,P<0.001
2.2 病情程度與血清及腦脊液NSE水平的關系
本次實驗表明,無論是血清還是腦脊液,同一時間點,GCS評分不同組間NSE含量相比較差異均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01),GCS 3~8分組的平均水平高于9~15分組的平均水平,表明GCS評分越低,NSE含量越高(表1、2)。
2.3 NSE與預后的關系
本次實驗表明,同一時間點,不同預后組的血清及腦脊液NSE水平相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預后不良組NSE水平高于預后良好組。預后不良組NSE平均水平在腦出血第3日出現驟升,且在第7日和第14日都保持較高水平,而預后良好組NSE水平曲線較預后不良組相對平坦(表3、4)。
表3 不同預后組血清NSE比較(x±s,ng/ml)
Tab.3 Comparison of serum NSE between the excellent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s (x±s,ng/ml)
與預后良好組同一時間比較,*P<0.001
表4 不同預后組腦脊液NSE比較(x±s,ng/ml)
Tab.4 Comparison of CSF NSE between the excellent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s(x±s,ng/ml)
與預后良好組同一時間比較,*P<0.001
2.4 血清NSE值與腦脊液NSE值的關系
本試驗表明,血清NSE與腦脊液NSE呈正相關(r=0.966,P<0.05)。
3 討論
出血性腦卒中的基本病理變化為腦血管壁的粥樣硬化,纖維素樣變性、壞死,致使血管壁破裂,顱內血腫形成,進而破壞腦組織;出血及其周圍組織水腫可壓迫鄰近腦組織結構,甚而發生腦疝,故該病具有較高的致殘率和死亡率。NSE是糖酵解途徑過程中的一種酸性蛋白酶,主要存在于神經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中,對維持神經系統的生理功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由于不與肌漿蛋白結合,較易釋放,這為腦組織損傷后檢測血清及腦脊液中NSE的變化提供了依據[6-7]。當缺血、缺氧、中毒或損傷時,由于神經細胞膜完整性被破壞,NSE從缺血或壞死的細胞中釋放出來,致使腦脊液NSE增高,由于血-腦屏障的破壞,NSE進入血液循環系統中,致使血NSE增高[8-9]。
3.1 NSE的變化機制
國外臨床研究發現[5,9],腦卒中后患者血清NSE升高可出現兩個高峰:起病后24 h內常有一短暫的升高,為初期腦神經元損傷所致;第二個高峰出現在起病后72~96 h,恢復較緩慢,可維持數天,為腦水腫及再灌注腦損傷所致。本實驗的研究結果表明,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14 d內),四個時間點NSE的平均水平于起病后3~7 d達高峰,這與以上的研究結果相吻合。研究還發現,隨著病情進展、不同的病情程度,GCS評分不同的患者血清和腦脊液NSE水平均于發病后7~14 d逐漸下降,NSE出現先升高后逐漸下降的過程,原因可能為,⑴NSE升高的原因:①腦卒中后早期,全身的應激反應狀態致使交感神經活性增強,血管收縮,從而導致腦組織缺血缺氧,神經細胞受損,膜崩解,大量NSE從細胞內逸出釋放入腦脊液及血液。②腦卒中后血-腦屏障受損,NSE可通過受損的血-腦屏障漏至血液中,這已被動物實驗所證實[10]。③血腫的直接壓迫,顱內高壓以及腦水腫可致缺血性腦損傷的級聯反應惡化,從而加重腦卒中的原發損傷,導致大量神經元壞死,引起或加重遲發性神經元損傷。④血腫內破碎紅細胞的降解產物,血紅蛋白的分解產物以及炎性介質等的毒性作用,均可致Ca2+超載、自由基連鎖反應加重[11-13]。⑵下降的原因:①腦卒中后機體出于應急反應,通過各種途徑使NSE的來源減少,并清除壞死神經元釋放的NSE,使NSE濃度下降。②在缺血、缺氧狀態下,由于神經元進行糖酵解,NSE消耗增加。③早期壞死神經元的NSE可能已經釋放殆盡[14]。④隨著病情進展,腦水腫在逐漸減輕甚至消退,腦組織的側支循環也逐步建立起來,出血所致的損傷逐漸趨于穩定甚至好轉,腦卒中患者開始進入恢復期,其血中NSE水平開始逐漸下降。因此,我們認為對出血性腦卒中患者早期檢測其血清和(或)腦脊液NSE能反映腦組織的損傷程度,NSE水平的動態變化可以有效地反映卒中后患者的病理生理變化,幫助了解腦原發性和繼發性損害的情況。Marchi等[15]也贊同這一觀點。
3.2 NSE與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的關系
血清NSE是急性腦血管病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有效指標,可以提示腦損傷的嚴重程度并決定患者的預后[16-17]。Cunningham等[18]的研究發現,出血后1周內血清NSE濃度較對照組明顯升高,升高的程度與病情的嚴重程度有關。本次實驗對GCS評分不同的兩組患者同一時間點的腦脊液和血清NSE值分別進行了比較,差異均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01)。這表明同一時間點,患者病情越重,GCS評分越低,NSE含量就越高。可見,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病情越重,死亡崩解的神經元越多,血-腦屏障受損程度越高,神經元釋放入腦脊液和血的NSE就越多,腦脊液和血清中NSE含量就越高。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出血性腦卒中不僅有NSE的升高,NSE的高低也反映了腦組織被破壞的程度和病情的嚴重程度。
本實驗亦表明NSE與患者病情的預后有關。研究發現,預后不良組病例血清和腦脊液NSE水平在病程各時間點均較預后良好組增高,而且在病程第7、14天仍維持在較高水平,曲線增長幅度較大,而預后良好組的曲線相對較平坦,說明預后不良組患者此時的繼發性神經元損傷較重,可能遺留有重度殘疾。此表明,NSE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示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早期預后,病程中NSE明顯增高者,病情兇險,如果NSE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則臨床預后不佳。與國內學者報道的結果基本一致[19-20]。
因此,NSE有可能作為藥物設計的潛在靶點,成為治療出血性腦卒中的有效途徑。病程中對其進行動態監測有利于醫師及時準確地評估腦實質被破壞的程度,提示患者的病程轉歸,以便及時地進行臨床干預。
3.3 出血性腦卒中患者血清與腦脊液NSE的關系
血液在血管系統內不斷的循環流動,是內環境中最活躍的部分,能夠通過溝通各部分組織液與外環境的交通來進行物質交換,因而人體各系統、組織、器官的病變可以在血液中得到反映。腦脊液主要由腦室內的脈絡叢組織產生,經循環回流入血液的靜脈竇,它在不斷地產生,又不斷地被吸收回流,由此循環反復,對神經系統起著支持保護的重要作用。血腦屏障在維持中樞神經系統的正常生理狀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生物學作用。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常引起血-腦屏障結構和功能的劇烈變化,致使血-腦屏障通透性增加。因此,血液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腦脊液的變化,而腦脊液的變化也能夠反映血液的改變。動物實驗發現,中樞神經元壞死、崩解后,NSE可以自胞質釋放入腦脊液,并通過受損的血-腦屏障漏至血液中[8]。本次實驗表明,出血性腦卒中患者同一時間點各自的血清和腦脊液NSE呈正相關,提示當腦組織發生出血性損害時,不僅腦實質遭到了破壞,使得腦脊液中NSE升高;同時血-腦屏障也受到了損傷,致使血清中NSE也升高,說明血清NSE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間接反映腦脊液NSE的變化,這與以上的研究相一致。研究還發現同一時間點的腦脊液NSE較血清NSE高(P<0.05),這種差異可能是由于不同病變部位神經元的易損性不同,距蛛網膜下腔的遠近不同,以及釋放出的NSE被局限或被消耗等影響因素造成[21]。
綜上所述,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血清和(或)腦脊液NSE為判斷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程度提供了定量信息。動態監測血清和(或)腦脊液NSE水平變化不僅對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病情的評估有幫助,對疾病預后、指導治療及療效觀察也有一定的意義,具有臨床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1]邵慧軍.腦出血急性期血清NSE測定的臨床意義[J].心腦血管病防治,2006,6(6):364-365.
[2]Yamazaki Y, Yada K, Morii S, et al.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erum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nd myelin basic protein assa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head injury [J]. Surg Neurol,1995,43(3):267-271.
[3]Greffe J, Lemoine P, Lacroix C, et al. Increased serum levels of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 epileptic patients and after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a preliminary report [J].Clin Chim Acta,1996,244(2):199-208.
[4]Weglewski A, Ryglewicz D, Mular A, et al. Changes of protein S100B serum concentration during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stroke in relation to the volume of stroke lesion [J].Neurol Neurochir Pol,2005,39(4):310-317.
[5]Schaarschmidt H, Prange HW, Reiber H. Neuron-specific enolase concentrations in blood as a prognostic parameter i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J]. Stroke,1994,25(3):558-565.
[6]中華醫學會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疾病學術會議.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J].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12(6):379-381.
[7]林堅,王懷甌,林逢春.兔腦出血急性期血漿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的變化及意義[J].中國實用神經疾病雜志,2006,9(1):41-43.
[8]Barone FC, Clark RK, Price WJ, et al.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creases in cerebral and systemic circulation following focal ischemia [J]. Brain Res,1993,623(1):77-82.
[9]Missler U, Wiesmann M, Friedrich C, et al. S-100 protein and neuron-specific enolase concentrations in blood as indicators of infarction volume and prognosi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J]. Stroke,1997,28(10):1956.
[10]Angelov DN, Neiss WF, Gunkel A, et al. Axotomy induces intranuclear immunolocalization of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 facial and hypoglossal neurons of the rat [J]. J Neurocytol,1994,23(4):218-233.
[11]Stevens H, Jakobs C, de Jager AE, et al.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nd N-acetyl-aspartate as potential peripheral markers of ischaemic stroke [J]. Eur J Clin Invest,1999,29(1):6-11.
[12],范生堯.腦出血患者血TNF-α、ET、NSE水平變化[J].中國神經免疫學和神經病學雜志,2006,13(4):250-251.
[13]王忠誠.王忠誠神經外科學[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368-379.
[14]毛向瑩.腦出血患者血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的動態變化[J].醫藥論壇雜志,2007,28(19):40-41.
[15]Marchi N, Rasmussen P, KaPural M, et al. Peripheral markers of brain damage and blood-brain barrier dysfunction [J]. Restor Neurol Neurosci,2003,21(3):109-121.
[16]Oh SH, Lee JG, Na SJ, et al. The effect of initial serum neuron-specific enolase level on clinical outcome in acute carotid artery territory infarction [J]. Yonsei Med J,2002,43(3):357-362.
[17]Lamers KJ, Vos P, Verbeek MM, et al. Protein S-100B, 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myelin basic protein(MBP) and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in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and blood of neurological patients [J]. Brain Res Bull,2003,61(3):261-264.
[18]Cunningham RT, Watt M, Winder J, et al. Serum neuron specific enolase as a indicator of stroke volume [J]. Eur J Clin Invest,1996,26(4):298-303.
[19]黃菊明.腦出血患者血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測定的臨床價值[J].心腦血管病防治,2006,6(1):16-17.